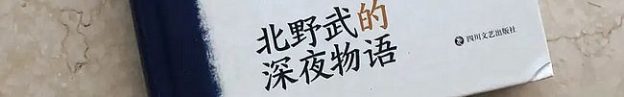【语文3班】
如果还有十分钟,陶渊明《桃花源记》这一篇,以及这个主题就可以讲完。
同一班里的学生,跨三个年级,又是三种不同的基础,能够黏合在同一个步调,只因有相同的状态——独立、努力和跟随。
【中文经典】
出国留学预备班中文经典,从《寒山子诗集》中拾得和寒山二人的名字入手,略讲“名相”和“色空”;从拾得和寒山所在的唐朝,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到宋时以“看脚下”开宗立派的圆悟克勤、虎丘绍隆到一休宗纯、村田珠光,一张禅宗印可状开启了“茶禅一味”的日本茶道;从禅宗的印心到现代科学“意识起源”之谜的探索。下课后,学生没有离场,提了两个问题:
1、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人类就拥有了神一样的能力,所以人工智能是无法取代人类的吗?
我答:我赞同这个问题的前半段,即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但并不代表人拥有了神一样的能力。就像元宇宙这个概念,似乎开创了一个平行空间,一个新宇宙,但这个宇宙是由人创造的,它的运行逻辑的根本,还是“人”这个根本。我不认为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类。如果AI掌握了可控核聚变,就意味着能量无限,人类对AI“拔插头”断电这个终极杀手锏将失效,AI什么时候会诞生自我意识?不知道。也许是十年后,也许是明天。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终极问题——如果我们的学习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一定会被AI取代,成为真正的工具人。我们要拥有的是AI无法、或短时间内还没有拥有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思考和创造力。
2、佛教和禅宗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提到佛教我都会听到禅宗?
我答: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禅宗又分为五宗七家,其中的临济宗是现在大陆佛教中分布最广的宗派。曹洞一宗,孤悬日本。禅宗作为佛教传入中土后迅速本土化的宗派,在唐时吸纳了当时社会文化精英的士大夫群体,从而正式融入并开始改造中国文化,成为和净土宗一样拥有广大信众的宗派。所以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由儒、释、道组成,而“释”,即佛家的代表就是士大夫阶层文化精英信仰的禅宗和民间拥有广泛信众的净土宗。禅宗强调“活在当下”,过去的不要去纠缠,过去的就放过自己;未来的不要去担忧,也不需要去为了还没到来的担忧,这就是活在当下。赵州从谂禅师人家问他什么他都答“吃茶去”,这就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事——吃饭去!
【八年级地理】
期末地理口试。学生抽签上台先后顺序和所讲主题。
表现均不佳。问下来,都去准备了,但一上台就大脑一片空白。我说当众发言,人人都会紧张,我也是。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双腿都在发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要多训练,相信自己,“无他,惟手熟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