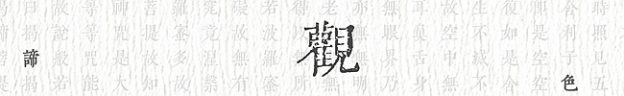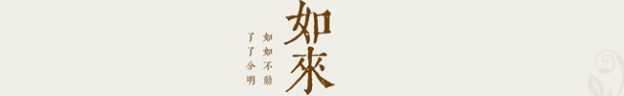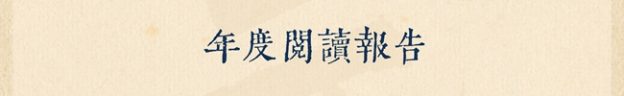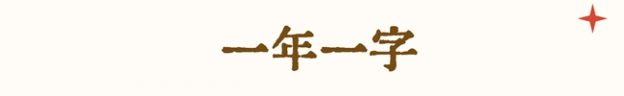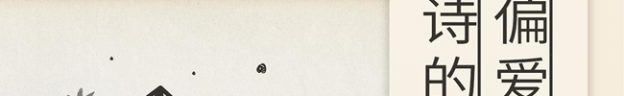学者们都不住在也闲书局附近,最远从家到书局,往返近四十公里。距离远了,路上遇到的状况就多变。多碰到两个红灯,或者天气不好车速慢一点,都可能会晚到,所以每次讲谈我都会从一个暖场的小环节开始,一面和已到的聊起来,一面迎接陆陆续续的到来。
今天的开场,是张可久的《殿前欢·客中》。张可久(约1270年~约1350年)高龄80,元从1271年在帝位争夺战中最终胜出的“叛军”首领忽必烈改元立朝到1368年大都陷落共98年,所以张可久也几乎是和元这一个朝代同兴共亡的一生。《殿前欢·客中》所写的,不仅是张可久一个人的人生,可能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前程渺渺,南来北往,功名半纸,风雪千山。张可久小令存世855首,占到元散曲的五分之一。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平均我们读到的每五首元小令就有一首是张可久的,但多数人一生就只能遇到一次张可久。一不小心,从忽必烈下令在中都东北郊外兴建庞大的皇城——大都——现在的北京,就是燕云十六州的中心之一,而这里就是宋、金、蒙古命运的纠缠之地,“飘”到了从宋建立之初,除了东面沿海,其余三面从北到南被契丹人的金(辽)、党项人的夏(西夏)、还有吐蕃和大理国,以及长江流域中下游的蜀(后蜀)、汉(后汉)、唐(后唐)等政权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宋能建立、延续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峰期,这是一个奇迹。
上周讲谈的“居学”有两项,一是从《诗经》里挑一首自己喜欢的译为英文,一是从张大春《见字如来》这本书里选一个字来说它的“前世今生”。
学者Tong的《无衣》(唐风)译文,真是美妙,让在英文世界生活了数年的小糜老师也赞叹不已。一首诗穿越两千五百年在今天被一位少年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多奇妙。
一人一字回到“语文”的源头,这即是“字,反映了每一历史阶段的现实处境和价值取向。字的意义,有时膨胀,有时萎缩,随时人而决。”(《见字如来》)
主题“诗以言志”,“走”过《式微》《子衿》和《静女》三首,并对《子衿》和《静女》做了对比,我说这就是古人的土味情话啊,各位。“两千五百年前的土味情话,怎么会这么文雅?!”有学者说。
上午的讲谈结束,学者问“居学”是什么,我说阅读,爱读什么读什么。“那这个可以吗?”Rudy举着一本曹雨的《中国食辣史》问。我说这本不错哦。根据作者的考证,中国最早开始吃辣椒的是贵州人。
下午的讲谈前半段,讲了《水浒传》前两回,为“鲁十回”做了铺垫。从高俅发迹到汴京之围;从王教头要去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鲁达在小种经略相公手下任职提辖,这个老“种”小“种”就是北宋的种(chóng)氏将门。
种氏将门的先人种放,本是钟南山的隐士,在山中过了三十多年的隐居生活。宋真宗因为他很有名望,特地将他召至京师,以示优礼文士,厚加宠遇,成为一时佳话。种放本以擅长经学和诗词著称,往来于嵩少、终南之间,出入朝廷,名气就更大了。但他无子嗣,侄儿种世衡在他的恩荫下晋身仕途。
赵匡胤依靠禁军的支持做了天子,思革五代武人跋扈之弊,于是宋初重文轻武。重要的武将,或其本身就是被制裁的对象,受扶植的又不见得有什么过人之处,稍有威望又马上面临制裁,如何选用将帅,可谓困难重重。同时北与契丹,西与李氏,以太宗时战斗力最强的禁军的实力,仍然大败者再,因此整个宋朝廷无法维持不信任武将而又同时对外作战的局面。外敌强大,不能不用武,用武便要有将,但又不敢太信任武人,文人知军事遂成为一种解决办法,既可免武帅跋扈,又仍可用智略继续与外敌周旋。
到宋夏战争爆发,宋兵屡败,兵将再次都成为问题。种世衡虽未经大战,但通过招抚番部建立了威信,又颇能运用智谋,于是从文人转为武将,并成为名将。他为种氏将门建立了良好名声,日后他的子弟继起为将,历仁、英、神、哲、徽、钦六朝,由此形成了三世将门,在北宋中叶以后的军事上担当着重要角色。
《水浒传》中“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指的应该就是种世衡的儿辈和孙辈中某两位,或许就是种世衡的儿子种谔与孙子种师道。但《水浒传》毕竟只是小说,考据起来,也未必就是如此。
后半段时间,一人一句讲完《史记·张仪列传》选,结束了主题“兵·法·纵横”。番外篇“战国·策”,讲了《战国策》中《文侯与虞人期猎》和《唐雎说信陵君》两篇。
上午和下午的讲谈,最后一个环节是送给各位学者和自己的新年期许——观自在。“觀”字左边表音右边表义,在白板上写下“見”“自”“在”三个字的甲骨文,“見”字是一个跪坐的人瞪着大眼睛,要见的是“自己”,跳出自己去看自己,看自己的情绪、感受和言行。这很难,但可以慢慢修行,慢慢靠近。人生中,只要做到哪怕一次,也能受益无穷。
这一期讲谈结束,下一期就要到三月再继续了。曾和一位常来旁听的家长说,在也闲的讲谈,每次我都是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临场发挥”,三分之一是在根据课程脉络推动。因为不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提出什么问题,而我要尽可能抓住这个时机去延伸和生发一点什么。这没办法准备,如果有,那就是时刻准备着,时机一来,机锋一到,就尽可能去接住,不要让它空过。但我总是挂一漏万。讲谈于我,是修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修自己的道。
离开也闲书局时淘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摄影家”丛书之一种,朱宪民《黄河等你来》。只差贺延光《眼光》和吴家林《边地行走》两种就凑齐这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