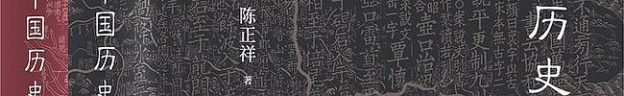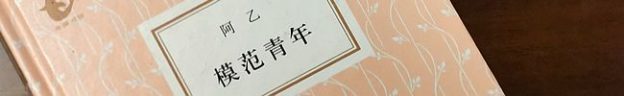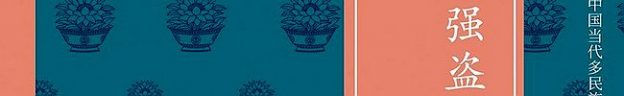自在幸福学堂代课,七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地理是历史的认知基础,历史是文学的诞生基础,要学好语文,就必须掌握一定的历史和地理基础常识。尤其是这个学期,初中的地理、历史(中国史、世界史)和语文都是我任教,这就更方便我在课堂上将三个学科融到一团。以至于在语文课上,有学生的作业是先去弄清楚一个历史时期,有的是要去在地图上找到某一山脉或半岛的所在,并分析其在军事和商业上的意义;在历史课上,有学生的作业是去了解一首古诗词,有的是用地理术语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的推进。所以新生会常有这样的疑问:这到底是语文课还是历史课还是地理课?我的回答是:都是。
作为文史地三门课的临时代课者,还好平时略有一点点阅读积累,但在实际教学中,仍感储备不足,力有不逮,就要刻意去填补这方面的不足。对我来说,最容易的方式还是读书。
断断续续一个月,翻完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的代表作,兼具现代地理科学的专业视角和宏阔的历史视野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虽然其中有一些历史原因导致的认知上的偏见或不足,但每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偏见里,也即是每个人的偏见成就了他,所以了解偏见也是学习和认知。
用时四个月翻张撝之《世说新语译注》,还是不能完全明白,但也收获不少。
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1版,2021年12月2印,一套上下两册,45万字。总阅读量1392本。
张撝之《世说新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版,总阅读量1393本。
下一本书,是一本大书,不单是开本、字数、内容还是影响,都很“大”——美国多所大学相关先修课程的首选教材,迈阿密大学地理学教授詹姆斯•M.鲁宾斯坦的《人文地理学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