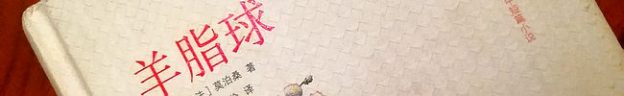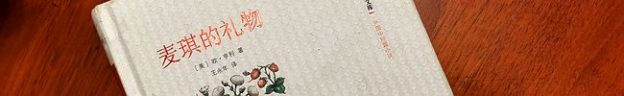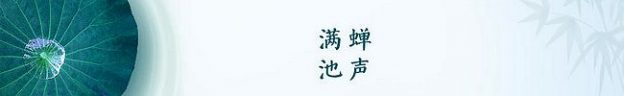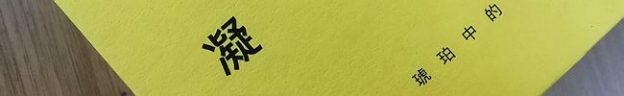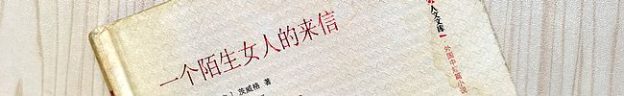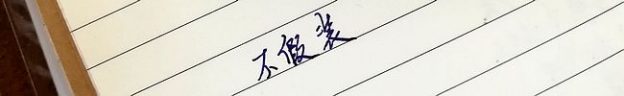早上六点,天亮没多久。打开卧室通往后花园的玻璃门,坐回床上,看着园子里的桔子树、黄瓜、辣椒,还有树下葱葱的十几盆铜钱草,想:如果今天是我这具肉身活着的最后一天,我要去做什么?
认真想了一回,千头万绪,又无从提起,还是决定做好今天应该做的。换了衣服,去叫女儿起床。
“昨天想过一个问题,我敲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是要给谁看?如果我想给谁或更多的人看,满足某种虚荣心,或搭建某种人设,就应该发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并希望有更多人来交流互动。可是我现在对发朋友圈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也关闭了博客的评论功能,我其实不想和别人分享什么,甚至有没有人看我都不关心,也不想假装成某种生活。”上班路上,我对坐在副驾的太座说。女儿在后座听喜马拉雅电台里的故事。
“这也是你的一种习惯,更在乎自己的感受。就像很多人写日记,不记录下来就总觉得这一天缺了点什么,就像我每天早上不练瑜伽就浑身不舒服一样吧?!”太座说。
“也是。我们的上一辈和我们自己,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之所以过得还算闲适,就是不怎么去和别人比,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不去比较就不会求不得,就不苦,就能找到自己。可能别人会觉得我这就是‘内卷’和‘躺平’了,但这也是有了比较。就像阅读,如果我想读原版书就要去学英文,那我想看的还有法国、德国、俄国作家的作品,我是不是要去学这么多语言才算不‘内卷’?那我又哪里有时间来阅读呢?跟那些一年也不读一本书的人相比,他们是不是也‘内卷’得厉害?我觉得‘内卷’和‘终身学习者’一样也是一个热门的伪概念。”最后我说:“中国过去的书那么多我都读不过来,二十五史这辈子能读一遍就大满足了。”
这两周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图书,建档。上周在小学部,这周在校区在生态公园里的中学部。中午从中学部步行去小学部和女儿一起吃饭,太阳晒得头顶发烫,在路上差点踩到两条蛇,大的一条约一米长,小的那条只有筷子长短,都是通体碧绿,脖子后两侧各三个黄色倒三角形图案,像是菜花蛇。边走边想,小的那条,这么细细的,它吃什么呢?
饭后,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在雨里走回中学部,整个校区就我一个人。操场一角,如麻的雨脚在师生建造的生态池塘水面上,踩出一阵一阵的鸡皮疙瘩。坐在图书馆窗下看雨,树上滴下来的雨也好像染到了叶子的颜色,满眼的都是绿。
午后清凉,蝉声满池,想起松尾芭蕉的俳句——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
今日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云门垂语云:十五日以前不问汝,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自代云:日日是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