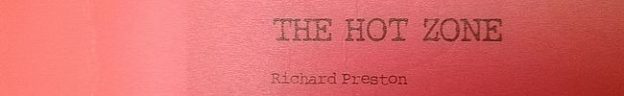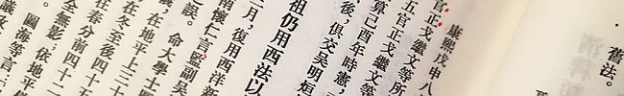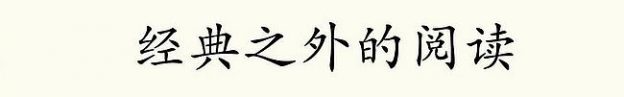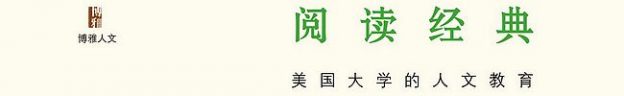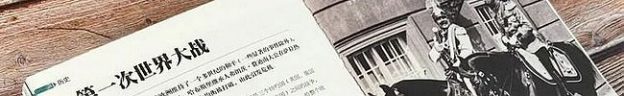我收回昨天对谢志曈译的杰弗里·瓦夫罗《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这本书的评价。
截止今天,豆瓣上这本书有88人读过,50人在读,给出评分的有105人,综合评分6.3分。考虑到读过这本书的88人中,像我一样认真读过的应该不会超过8人;给出评分的105人中,刷书评的“书托”至少有10人(给出满分并且短评、书评满是溢美之词的新注册用户尤其可疑),这本书目前的评分还是高了,预计最终会在4.5上下。
这本书在翻译上一塌糊涂,甚至校对也大面积翻车,大量的翻译语句不通和重复啰嗦让我怀疑翻译者“谢志曈”其实只是理工大学出版社找的某个“机翻”者的假名。
早上七点,我从昨天读到的第一百零八页“伯罗奔尼撒战争”继续开始时,之前的错误率和让人莫名其妙的话出现的频率还勉强能够忍受。“一百万字,出错率稍微多一点点也还是能忍受吧?!”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还在最后的环衬页写:“满分五星,给这本书三星的综合评分。给作者驾驭这宏大题材的能力一星;给地图、图片的印刷质量一星;给装帧设计一星;翻译不佳,扣一星;校对还可以再仔细点,扣一星。”
往后又读了几十页,错误越来越多,我又在环衬页写了:“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选一位能与之匹配的翻译者?责任编辑有通读过这本书吗?没有吧?!”
最后读到二百六十九页,我放弃这本书了。在环衬页写:“读不下去了。错误、漏字、语句不通、译文莫名其妙至少超过两百处。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绣花枕头”书,精美的装帧里是一团糟的译文。综合评分最多也就一星半,一星给印刷、装帧,半星给可能还不错的原著。”
抄列出以下几句书中原句,以证这本书译文的糟糕:
《旧约全书》的描述使犹太地区反抗巴比伦统治,及他们的人民和耶路撒冷地区的遭遇,远比其他故事更为人所知。(P.93)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远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巴比伦城,并攻占了巴比伦城。(P.98)
波斯军队由步兵、战车和骑兵组成,统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其军队成员复杂构成。(P.99)
罗马开始从一个危机滑向另一个危机,甚至面临奴隶起义重大的挑战。(P.139)
410年,罗马被第一次浩劫。(P.160)
441年—453年,匈人军队在阿提拉的率领下袭击西罗马,后来在哥特人的帮助下被埃提乌斯击退。(P.165)
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罗马世界政治上发生变化。(P.190)
尽管佛教摒弃了《吠陀经》的权威,但后来从吠陀文献中借用了业报和与轮回的双重思想。(P.196)
来自各地的异域珍奇纷纷涌入杭州市场,为皇宫和政府各部门提供商品及服务的交易超过100宗。(P.243)
用以支撑丹麦国力的,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各种贸易的经济活动,诸如日德兰半岛东南端的海泽比和西海岸的里伯。(P.258)
图卢兹的雷蒙德四世接受教皇乌尔班二世的祝福。他第一批响应教皇乌尔班夺回耶路撒冷号召的人之一。(P.269)
还有“公元378年,哥特人暴乱,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战胜罗马军团,但于383年被制服。”这样“公元XX年”和“XX年”时隐时现的不统一或被“弄丢”的“公元”不下一百处。
根据2019年3月1日起施行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超过1/10000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1/10000以上5/10000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差错率在5/10000以上的,出版单位必须全部收回。这本书的差错率,绝对是编校质量不合格的,但现在还在各种公众号上投放软文,我就是在某公众号上读到软文入手的。定价二百九十八元,以不到定价五折的一百三十九元购入,现在我觉得它应该只值十八元——称重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