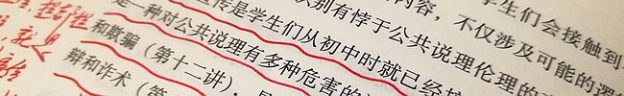早上六点起床,洗漱、早餐,读书。读完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最后两章。在书最末的三百二十七页“后记”半页空白处题跋: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十天看完这本书。没什么大道理,都是些朴实的话,通常的道理。然而,越重要的越简单也就越不简单。今年读完徐贲的书?十几本如果读完,今年我的阅读就是“徐贲年”。
二〇二一年,我有图文记录的连续不间断独立博客(Blog)已进入第十七年。博客日志的阅读量从开始只有自己写自己读的个位数到超过两千七百万,用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脱离对公共事件的参与和评论,隐为半私人的记录至今。今天读完《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才发现我一直在进行的其实是一种“业余而独立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在我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状态下,培育了我公共对话的能力和独立精神(或者是我认为的独立精神)。
“我们知道,媒体将最大的篇幅和时间以及最大的荣耀给了最少的人,甚至吹牛撒谎的人依旧层出不穷风起云涌并大行其道被炮制成神话。我的日常记录,只试图将历史还原于个体,并把个体展开于日常生活,从而把不可复现的历史记忆和宏大逻辑深植于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之中;那些被忽略的,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们,在重重阴影中他们的日常活动远较个别的、传奇的历史事件更具本质意义,正是他(我)们从过去塑造了现在。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引人注目的人和事,不过是漂浮在时间河流水面上的泡沫。”当年这段我开设博客的“独白”,和那些每天敲下的随笔(日志),似乎已具有了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的意味,并为我博得了小小的声名。现在回头看这十几年的随笔,十分日常琐碎,但还幸基本算是语句通顺。我们都知道“不管专业知识多么高深,多么有创见,说理表述所需要的基本逻辑、语言要求仍然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基本的文通字顺和可靠逻辑,再了不起的思想也没有说服别人的手段和力量。”(P.6)
威廉·赫兹里特说,随笔“把思想的才能与资源运用于人的事务,这种写作虽然不属于艺术、科学或职业,却属于作者的认知范围,贴近人的事务和关怀。”以人的事务为题材,这是一种人文的写作,一种非专业的,独立于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写作,“在道德与方法上正如实验之于自然哲学,与教条的方法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业余”的写作,它强调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个人的独立观点。它拒绝接受任何宗教或政治教义的束缚,它让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成为自己的声音,这种业余而独立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要鼓励的。(P.201)而独立、平等和自由的表达,正是我所认识的如今已所剩不多的独立博客(Blogger)们所信奉的“独立博客精神”。
任何行业或手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都(应该)有一位创始者,即中国俗话的“祖师爷”,例如鲁班被视为土木建筑和戏班的祖师,黄道婆被认为是中国纺织业的祖师。博客这种随笔的写作形式,祖师或许就是法国作家蒙田。
“随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写作形式,这个传统具有人文意义,帮助形成了与今天人文素质教育有联系的写作形式。随笔是一种体现主体意识的个人写作,它无需遵守任何宗教、政治的教义和教条,写作者可以自由陈述自己独立见解和看法。它平等地对待读者,是写作者在“试着”说服他人,坦诚、平和、真实、理性,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自由谈”。蒙田是第一个称自己的写作为“随笔”的,他说自己是在尝试着把真实的想法以合适和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随笔培养的是仔细阅读、思考、分析和理性说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写作不把写作只当作一种私人的文字,而是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这也就是说,写下来的文字是给别人阅读的,作者有责任清晰而有理地的表达自己的看法。(P.182)
当然,中国过去的人们也有类似的写作,如明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但我认为这些随笔大多囿于个人私空间里小趣味的“私写作”,缺乏了“公共对话”的功能——“公共说理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中,长期遭到忽视。我们的写作教学,主要以某种空洞的抒情为其特色,而在说理方面,则明显训练不足。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其中最优秀的学生,亦主要擅长‘私语’写作。”徐贲的书,正是弥补此一缺陷的极佳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