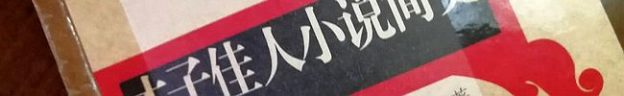谭帆的《古代小说评点简论》,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从书”一种,2005年6月1版1印。定价8元,旧书,不记得多少钱在哪里买的,但肯定低于定价。
最近看的《古代小说评点简论》《古代小说版本简论》《才子佳人小说简史》三本小说简论简史,主要参考书目里,都有一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的这本《中国小说史略》太好,还是因为是“鲁迅”的缘故所以特别重视?好奇。我的“鲁迅”已经死在课本和老师手里,但这个“鲁迅”似乎不太一样,不读一读是无法判断的……忍住,一定要忍住,这三个月是不能买书的,一本都不行。一分钱都不行。
“在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中,金圣叹的影响至大”,我书架上金圣叹“六才子书”有《水浒传》《西厢记》《杜诗》三种和《唐诗》。这些书几年了一直还没好好看过,只是读其他书遇到相关内容就抽出来翻检一通。时间不够啊!
当初买金评本《水浒》,是因为小时候看过的是一百二十回本,金评本只七十回且也独立成书并流传,这是一个怎样的版本?好奇。买金评《唐诗》,是全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蘅塘退士选《唐诗三百首》是现在流传最广的版本,金评《唐诗》选六百首,孰优孰劣?各自选诗的标准是什么?好奇。买金评本《杜诗》,徐子能咏杜“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晚年律更细,独立自苍茫”;金圣叹“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杜诗1400余首,金圣叹选批的都是哪些杜诗?好奇。别人好奇害死猫,我一好奇害钱包。
一本《古代小说评点简论》,也是一部古代小说评点简史。几百年的众多人物和作品的简史简论,区区6万字实在是简之又简,但对如我闲散读者来说,入门也还是嫌太长。为读完后再次消化,顺便也再做个简化,就有了下面2600字的梗概:
文学评点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从时间而言,大致从唐代发其端,南宋走向兴盛,历元、明、清三代,至晚清才退出历史舞台。就文学形式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体都有评点出现,如诗、词、曲、赋、文、小说、戏曲等;更有甚者,中国古代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几乎都经过了评点家的批点,有的还是一批再批,《诗经》、《楚辞》、《史记》、《汉书》、李白、杜甫、东坡、稼轩、《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巨作在其自身的传播史上都留下了评点者的深深痕迹。
通俗小说评点萌生于明代万历年间,兴盛于明末清初,是中国传统的评点形式在小说领域的延伸,而古代的文学评点形式又是以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为基础的。从总体而言,小说评点得以在形式上成熟,源于三方面的因素,即:注释、史著之体例和文学之选评。
与所评作品勾连在一起的评点方式源于对典籍的注释,而在中国古代最早得以注释的一批典籍是儒家的经典,即《易》、《书》、《诗》、《春秋》、《礼》、《乐》。“经”在中国古代有着很高的地位,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故中国古代的注释是由注经开始的,这种注释对后世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尤其是注文与正文融为一体是后世小说评点中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的直接之源。
史著之体例对小说评点的影响亦甚大。这种影响主要支自于史著的“论赞”。“论赞”作为史著的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是史学家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直接评述并且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形式。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于《左传》。《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形式上是一部《春秋经》的传。它是以《春秋》为纲,博采史实,加以编订的编年体史籍。在《左传》中,作者不仅详记史实,还“”记录了古人对史实的评价,一般泛称君子曰。在司马迁《史记》中,这种形式有了明显发展,《史记》每篇篇末均有署为“太史公曰”的一段评语,表达作者对篇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以后这一形式遂成定制。
小说评点的产生赖于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相对繁盛。嘉靖元年(1522),《三国演义》结束了长期以抄本流传的形式而公开出版,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流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后不久,同样产生于明初的《水浒传》等也得以刊出。从“抄本”到刊行,古代小说就其传播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同时也为小说创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在嘉靖元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近百年中,通俗小说的创作逐渐兴盛并得以平稳发展。据现存资料考知,此时期共出版通俗小说五六十种。这虽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但在通俗小说的初创期这已是一个不容轻视的现象。这一时期,古代通俗小说的四种基本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都已完备,各自出现了一部代表作品,这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四部被时人称为“四大奇书”的作品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万历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源头,它对小说评点的发展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小说评点之所以能在后世的小说理论批评和小说流传中起到重要作用,乃是由万历时期小说评点的文人参与和评点的商业化所决定的。
万历时期的小说评点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一方面,评点从万历时期引入小说领域,随即就形成了一个颇为兴盛的局面,它与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如果说,万历时期是通俗小说走向兴盛的起始,那这一时期同样也是小说评点的奠基阶段。同时,万历年间又是小说评点形态的定型时期。它在小说评点的形态特性、宗旨目的等方面都逐步趋于稳定。
万历二十年(1592) 左右,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颇为重要的年月。正是在这一时期,有两位中国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的重要人物开始了小说活动,这就是著名文人李卓吾和著名书坊主人余象斗。这两位重要人物同时开始小说评点活动,仿佛向我们昭示了中国小说评点的两种基本特性,这就是:以书坊主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商业性和以文人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自赏性。小说评点正是顺着这两种主要态势向前发展的。
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承万历小说评点之绪而呈发展壮大之势,这是小说评点由萌兴走向繁盛的百年。同时,小说评点也在此时期渡过了它的黄金岁月。所谓明末清初在本文中主要是指明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四朝的一百来年。这百来年是古代小说评点最为繁盛的时期。这段时期,小说评点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小说传播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且评点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可以说,小说评点史上有质量、有价值的评点著作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并公开出版的。
在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中,金圣叹的影响至大,他的评点使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黯然失色,在他的影响下,小说评点名作迭生评点风气被推向高潮。因此从明天启到清康熙年间,小说评点形成了百年奇观,这是小说评点史上最为丰硕的百年,也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黄金岁月。
光绪三十四年(1908)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铅印出版。该书封面顶上小字直书“祖国第一政治小说”,以明其评点之宗旨。其实此书与其说是评点小说,倒不如说是借小结评点来表现其政治理想。
燕南尚生对《水浒传》的所谓“新评”充满了政治说教的色彩,而其对《水济传》的“命名籍义”更可谓登峰造极,如释史进:“史是史记的史,进是进化的进,”言“大行改革,铸成一个宪政的国家,中国的历史,自然就进于文明了”。这种任意比附、牵强附会的所谓“整义”,在《新评水浒传》中可谓比比皆是。这其实已经把小说评点沦为表达个人政见、表现政治理想的工具了。由于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故《新评水浒传》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可以说,它是小说评点史上一部最后的“名作”。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历经三百余年,至此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总体而言,小说评点的式微有评点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影响。就内部因素来看,晚清小说评点的草率和鄙陋是小说评点逐步失去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报刊小说带有“补白”性的所谓“评点”则使小说评点沦为可有可无的“角色”。而从外部原因来看,晚清以来,小说渐由传统的“边缘“逐步跃升为文学的“中心”,也使得小说研究方式突破了传统格局,“评点”这一专注于个别文体的批评体式已不适应对小说的全方位研究。尤其是“小说界革命”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形式,于是伴随报刊形式而共生的“论文”、“丛话”等形式逐渐占据了小说批评的中心舞台,故小说评点的“让位”已成必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