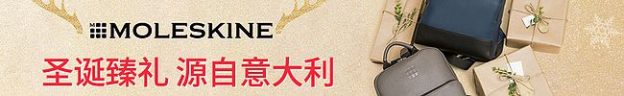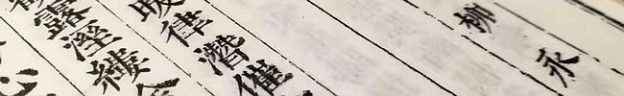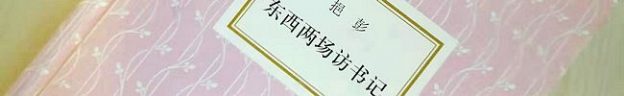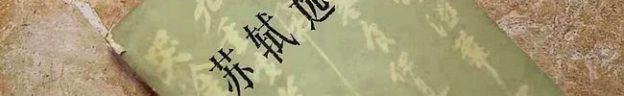一周都是晴天。昨天周五,下午没课,绕着学堂中学部后山转了两圈。3公里的山路上,红黄绿的叶子在午后的阳光下筛出满满斑驳的影子,最是一周里惬意好时光。
贵阳这个冬天,晴天比往年要多,也好,也不好。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那就很可能会在不该下雨的时候在下雨。
周五晚饭后照例是进“城”买菜逛书店。花卷病了一周,昨天不再发烧了,在爷爷奶奶家休息;太座去剪头发和买菜,我一个人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淘书。
每周淘书都有收获。这个收获不一定是非要买到书,即便是没有买书,淘书这个过程也是乐趣多多。
在二楼旧书区,先是找到一本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繁体竖排硬皮精装《鲁迅小说集》,是《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合集,560页里收录了鲁迅全部的短篇小说,所有篇目的编排都是依照鲁迅自己原来编订的次序,大爱。纸张泛黄,印刷精美,扉页上还有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1956年6月17日和1967年11月3日这本书前两任主人留下的藏书记录和个人印章,更大爱。新书固然悦目,但有了阅读印记的旧书更加让人喜爱,因为这里面还有其他人的人生记忆和时间碎片,这实在是一种特别的邂逅——人与书和人与人的邂逅。我几次拿起又放下,犹豫的是书的品相不甚佳和价格也不低。这本书定价1.9元,标价40元。即便是现在,一本同样内容的精装《鲁迅小说全集》新书也只标价不到30元。这本书的硬壳封面封底已磨损严重,四个直角都磨成了圆角还露出了内芯,书脊的蓝布也已朽坏,内页多霉、污渍。终于我还是没有买下带走,我知道它就在哪个书架的第几层,或许哪次再见我会忍不住带走。
转身,在另一个书架最底层,寻得一本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词学家和宋代文学专家刘乃昌是现代词学开拓者和奠基人夏承焘的弟子,不知道为什么刘乃昌的《苏轼选集》2005年以后就没有再版了。
想必这本《苏轼选集》的前任主人是一位爱书人——不是摩挲感慨后插架收藏的那种,而是有书必读,生活不可无书甚至可能书不离手或者家里、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以至于喝茶吃饭随手就抓一本书来垫杯碗的爱书人,所以书的封底上像奥运五环一样大小嵌套着几个杯碗底油渍。油渍里还浸润有一个歪歪斜斜1*2cm印反了的蓝色售书章,只依稀辨认出“书店10售书章”几个字,至于书店名则是和油渍霉斑融为一体了。除了油渍,霉斑还从封底一直顽强穿透60页,243页一本书,最后文选部分的页脚都已破损,想来这一餐的油水一定充足。
虽然这本比我小不了几岁的《苏轼选集》除了自然旧的纸张黄脆,品相要比《鲁迅小说集》还要差许多;虽然这个版本的选集里没有我最喜欢的那首诗,但我还是欣欣然带走。除了定价0.9元,标价5元,价格合理——这样品相的书只能论斤卖但我还是按本买,这样算起来价格并不合理;但现在早餐一碗肉沫面都要11元,面下肚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化为粪便,而一本书价还不到半碗面条,还可以不断翻阅数年直至碎成片片蝴蝶,这个价格就很是合理了——还因为这个版本选的诗《琴诗》、词《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和文的《留侯论》、前后两篇“赤壁赋”、《喜雨亭记》都是我喜欢的,另外《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两篇,如果我后续还继续上中学文综(地理、历史和语文综合)课的话,也是语文教材篇目。所以与其相请,不如偶遇。
苏轼一生写诗二千七百多首,在我读过不多几首里,最喜欢《赠王仲素寺丞》,博客名“尺宅即江湖”的“尺宅”来源之一就是诗中“尺宅足自庇,寸田有余畦”句。可能《赠王仲素寺丞》在苏诗中并不突出,所以昨天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找到的三个版本的苏轼选集中都不见,而我又不舍得为了一首诗购一套《苏轼全集》——或许等我有钱了会的。
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