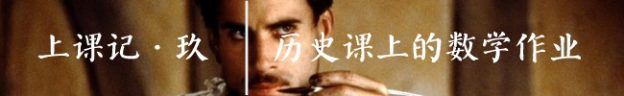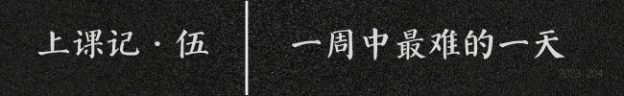【语文3班】
连堂,继续主题二十四“三国の对·策”。讲完孙权与鲁肃的“江东对”(榻上策)。
课程引子“建安十二年(二〇七),曹操讨伐乌桓胜利,班师途中登临碣石山时作《观沧海》,并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辽东太守公孙康杀袁尚、袁熙;刘备三顾茅庐,刘备之子刘禅出生。”重温曹操《观沧海》,为下一主题“建安风骨之三曹七子”作铺垫;公孙康杀二袁源于官渡之战袁绍战败,为七年级历史第16课新课“三国鼎立”作铺垫;从刘禅引出赵云原为公孙瓒近卫骑兵“白马义从”之一员,《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三国志·蜀志·赵云传》、《三国志·蜀志·二主妃子传》和《三国演义》中在长坂坡“单骑救主”的故事,并播放电影《三国之见龙卸甲》(赵云传)中“单骑救主”片段;然后从刘备三顾茅庐开讲《隆中对》(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节选)。
作业方面,W每日十分钟的字帖练习,从开始的抗拒到现在用毛笔在写簪花小楷,已渐入佳境;L不紧不慢,正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中;Z和S在鼓励和加强他们的思考分析和口头表达强项,书写只要求尽力就好。
Y关于上海马拉松的那篇文章,在经十一次修改后,只需要完成标题的修改和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补充就完成了。Y在一篇文章经十一次修改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他对任课者的信任、跟随和坚韧的态度,以及同样重要的绵长的学习力道。我仍然期待着,明天就能够把早已准备好的那个“A+”给他。
【八年级历史】
第六单元第19课:七七事变与全民族抗战,重温了“九一八事变”,梳理了“抗战八年”和“抗战十四年”同时成立而又不同的原因。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7月29日北平失陷;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投入兵力近20万,中国投入超过70万兵力,最终败北。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日军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兵临城下,从两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和日军的推进速度来分析抗战初期,中日军事力量的对比。Z提出,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已占领沈阳。进而占领东北,完全可以走海路,那样应该会更快抵达上海。于是我们就日军为什么没有选择海上航线,而是在陆上推进这个问题,结合史实展开讨论。
【七年级历史】
完成第四单元第16课:三国鼎立一课中“官渡之战”一节。简单了解教材内容后,就教材“相关史事”中“袁绍拥兵10万,战马万匹,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以及“袁绍谋士许攸降曹告之袁军粮草屯于乌巢,曹操率兵偷袭乌巢大破袁军。”两句,提出我的个人见解并分析和提出依据——
官渡之战,曹袁两军并非一强一弱,而是势均力敌。
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关于官渡之战,裴松之有注: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按《钟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余匹,繇马为安在哉?
这段注说的是曹操起兵时已有五千的兵力,之后胜多败少。破黄巾军后“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这里的说法不严谨。曹操并没有全部接受三十万投降的黄巾军,只是“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以当时曹操的实力和黄巾众的战力来看,“青州兵”的兵力不会超过一万人。就算征战损伤,裴松之认为曹操的军队人数也不应“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这么少。并且,“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曹操就算不懂临机应变,也不至于以仅数千的兵力长时间与十几万人对抗。袁绍军队扎营数十里,曹操也能“分营与相当”,这样的兵力也不会少。
第二,如果袁绍的兵力是曹操的十余倍,自然会将曹操的军队围困。但这期间曹操派徐晃袭击袁绍的运送补给的车队,曹操又自己出击淳于琼,这说明袁绍的兵力并不能压制曹操,也又说明了袁曹的兵力虽不至于相当,但至少不至于相差十余倍。
第三是“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各种记载都说曹操坑杀袁绍的士兵七八万人。八万人溃散奔逃,八千人怎么可能将他们抓获?并且袁绍的溃兵也不会束手待毙。所以由此得知,曹操的兵力也不会是仅有数千人而已。
最后按《钟繇传》的记载,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钟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到曹操军中以补充军用。但《本纪》及《世语》的记载都说曹操当时只有六百余匹马(骑兵),那钟繇送至军中的还有一千多匹马去了哪里?
所以,官渡之战极大可能不是一场“历史定论”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更有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霸之战。这一战的胜利,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奠定了基础。那既然是势均力敌,并且曹袁两人身边都有大量的战将和谋士,曹操缘何取胜,袁绍又缘何失败?原因就在“从”与“不从”上,也就是袁绍身边沦为花瓶的智囊们。
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一战,胜者几年后统一了北方,败者七年后于病中抑郁而死。
曹袁两人身边都有大量的战将和谋士,曹操缘何取胜,袁绍又缘何失败?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从”与“不从”,即是否采纳智囊谋士们的建议上。
先来看《武帝纪》中曹操是如何对待谋士们提出的建议的。
兴平元年,袁绍想与曹操结盟讲和。当时曹操“新失兖州,军粮尽,将许之。”失地又缺粮,强敌此时却来讲和,难得的休养机会,所以曹操准备答应下来。但这个时候“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程昱劝阻曹操,不知道程昱说了什么(程昱传中或许会有),曹操竟然听了。
建安元年,“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这里曹操是有自己的主见的,同时也参考和采纳了荀彧、程昱的建议。等迎到天子,“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定都于许昌,这是曹操和谋士们早就定好的一步棋,所以这里曹操采纳董昭的建议,也只是顺水推舟。
曹操善于采纳别人的建议,并不代表他没有主见。“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这个时候确实不能杀刘备。一来敌人的敌人就是可以拉拢的对象,现在正和吕布开战,吕布占领了刘备的根据地,走投无路的刘备来投奔,正省去了一番“统战工夫”;二来不论刘备是否有雄才,凡来投奔的都好好收留,正是曹操一贯“唯才是举”的风格。所以,这次曹操没有采纳程昱的建议。但随后“术欲从下邳北过,公遣刘备、朱灵要之。会术病死。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公悔,追之不及。”曹操这里确实是糊涂了。人才不为自己所用,也可以像徐庶一样留在身边,至少保证不为他人所用。这一留一放,等于是开了一桌流水席,让刘备在这里吃饱喝足抹了抹嘴角的油就走了,还被顺走了一些兵,不悔才怪。
“兴平五年春正月……公将自东征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这次曹操亲征反贼刘备,诸将都不赞成,但郭嘉支持曹操,于是击破刘备军,还生擒了夏侯博。刘备抛妻弃子,只身投奔袁绍。要论《三国志》里谁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会逃命的小强,非刘备莫属。
兴平五年“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公从之。”这一次的战果是不但斩杀了颜良,顺势解了白马之围。
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袁绍起土山,军士居高临下射杀曹操营中士兵,箭如雨下,在军营中往来行走都要靠大盾牌遮挡,士兵都非常恐惧,并且这时候粮食也不多了。曹操想退兵,写信征求荀彧的看法。荀彧回信说了一番鼓励打气的话,总之就是劝不要退兵。“公从之”,曹操听了。
不久“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随后“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袁绍的谋士许攸贪财贪到连袁绍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于是转来投奔曹操,并泄露军机让曹操袭击淳于琼。曹操怕不怕许攸是来诈降赚他入彀的?不怕。一是因为他的首席谋士荀彧在之前的信里说过袁绍“能聚人而不能用”;二是许攸只是贪财,但不傻,还没到为了钱财不要命的程度,当然就不会投奔必败的曹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曹操的兵力并不会比袁绍少太多,更不会是《武帝纪》中所记的仅只数千人对抗十倍于己的袁绍。如果曹操此时只有数千人,迟早必败,许攸又何必冒着生命危险来降?所以曹操信许攸,于是“大破琼等,皆斩之……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曹操最终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
在《三国志·董二袁刘传第六》的《袁绍传》中,袁绍并不缺谋士,他有与曹操相当的智囊团,但对待谋士们提出的建议,只有一个态度——不从。
在曹操迎天子之前,袁绍的谋士郭图就劝袁绍迎天子并立都于邺城。绍不从。
击破公孙瓒后,派长子袁谭主理青州事务,谋士沮授劝袁绍说不可以这样,否则“必为祸始”,绍不听。
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后方空虚,田丰建议袁绍出兵抄曹操的后路,这是多好的机会和多好的计谋。但袁绍因为小儿子生病了,所以“不许”。
官渡之战,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进攻白马。沮授又劝阻袁绍说颜良性子急又心胸狭隘,虽然勇猛但不能独当一面。“绍不听”,颜良被曹操斩杀,士气低迷之际,沮授再次提出建议,说我们虽然人多,但不如曹操的兵勇猛。现在他们补给不足,周转不利,急于速战速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慢慢折磨他,和他打持久战(“宜徐持久,旷以日月”)拖垮他。结果,绍不从。
淳于琼带上万士兵向北运粮而来,沮授建议再派蒋奇带领一支军队在周边巡逻,以防曹操再来劫掠。结果还是“绍复不从”。大败。
田丰曾经劝过袁绍,如果要与曹操一战,最好是持久战辅以奇兵骚扰,“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如果袁绍按照这个作战计划进行,曹操早就嘎掉了。但“绍不从”。败回到冀州,“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杀掉了田丰这个大冤种。田丰应该算得上是袁绍身边的准一流谋士了,因为他不但知道谋胜、谋生,还知道自己的谋略不会被采纳,以及还能“谋死”——知道袁绍回来一定会杀了他。
所以,如果说官渡战前和战中,曹袁双方的军事实力略有高低的话,在谋士阵营完全可以说是势均力敌。最终曹胜袁败,正是俗话说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