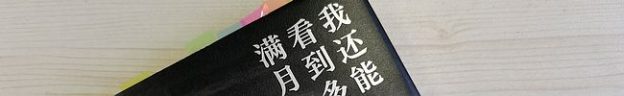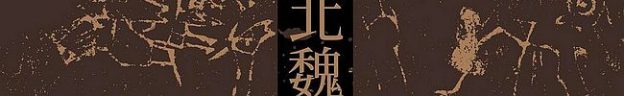2014年,62岁的坂本龙一(1952—2023)罹患口咽癌后,又被诊断出了直肠癌,并且癌细胞已转移到肝脏和淋巴。于是不得不坦然面对和思考自己生命的终点——死亡。这本书就是记录坂本龙一对死亡的思考和慢慢死去的过程的记录。
书名《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来自电影《遮蔽的天空》中一段台词:因为不知死何时将至,我们仍将生命视为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一生所遇之事也许就只发生那么几次。曾经左右过我们人生的童年回忆浮现在心头的时刻还能有多少次呢?也许还能有四五次。目睹满月升起的时刻又还能有多少次呢?或许最多还能有二十次。但人们总是深信这些机会将无穷无尽。
其间,坂本感到“现在支撑日本人生死观的‘脊梁’似乎都已经消失。所以我正努力从听闻的藏传佛教故事中收集有关生死观的片段,来思考自身的死亡问题……人类能活到八九十岁,也就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吧。想到人类长达20万年的历史长河,想到没有高科技医疗的时代,我真的不确定到底是否有必要为了延长寿命而逼迫自己接受治疗。”坂本“拒绝痛苦的治疗,只接受最低限度的护理以迎来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价值观,也正是我在自身所奉行的。太座五年前罹患甲状腺癌,手术后恢复得还不错,所以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而我在三年前的一次例行体验中被医生告知“情况不太好,建议去三甲医院做检查”。于是在疑似淋巴癌晚期、肺癌晚期、胃癌晚期、直肠癌晚期的一通检查,仍然无法确定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后,我也选择了“与癌症共生”而不是“与癌症战斗”。每年新年到医院确认一次自己是否患上各种癌已成“惯例”。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即使强行战斗也没有意义。”因为“我深深地觉得,人类创造的一切最终都会被毁灭,认识到人类根本无法与自然抗衡。”
在死亡面前,才是众生平等。坂本龙一的《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不过是一些细碎的随笔,称之为“坂本记录自己如何死去的碎碎念”应该也合适。
坂本龙一《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中信出版社2023年6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0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