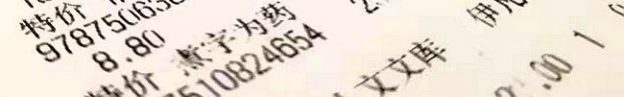关于贵州,如果在这个书店都找不到你想要的书,那就不用去其他书店找了。因为这个书店,是目前贵州最全的有关贵州的书的书店,也是我最喜欢的书店。昨天晚饭时我对侄儿洪说。
这家书店,就是“五之堂书店”团队与贵州龙企业集团合作,在贵阳的卫星城新添寨CBD——“里外里”商业街比之前五之堂书店“面积大三分之二”,2月19日元宵节试营业,28日正式开业的新书店。
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意,一个人都会有学名和小名。我初中班上有个男同学就因为他“王华”的姓名让人感觉太雅,于是整整三年他都相信自己就是大家嘴里的“王二狗”。书店也一样。新书店的学名是“贵州龙二十四书香书店”,不过就连书店老板和店长在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里也只说“二十四书香书店”,就像读者买书时通常不会给店员说:“请给我一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复活》”,而只是问托尔斯泰的《复活》在几楼的哪个书架。
在二十四书香书店到来前,我新添寨有两家书店,一家是席殊书屋,一家是新华书店。两家书店相距不过百米,都在主干道上。席殊书屋主打教辅。新华书店到了这里就成了农家书屋,窗不明几不净,灯光昏暗,玻璃大门几年没擦都脏成了毛玻璃,只有门把手还保持着光泽,还每个月最后一周准时来“大姨妈”——关门盘点。所以,二十四书香书店,是我新添寨第一家真正的书店,独立书店。我有一种所居住的乡村一下成为文化中心的不真实窃喜。
书店开业前的大量准备工作需要很多人手,五之堂团队人手不够,并且这是我最喜欢的书店(没有之一)。为了这心头好,自私的我一定要做点什么——就像喜欢的包子,总忍不住要多口服一枚,如果这家店不买包子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那我怎么办?我以后去哪里吃包子?你不卖包子?那不得行!我不同意!所以书店老板秋蚂蚱说过:“做书店的人大多有病,我在书店对我的老顾客也说:买书的人也大多有病。一旦染上这种病,很难治愈。卖书的和买书的是一对病友。书店是惺惺相惜的‘病房’。没有一个纯粹的书店,我们到哪里去‘病着,且快乐着’”?
有病得治。我的病灶在书店,我就得去书店。
过去四天,我一家人每天在二十四书香书店做半天义工,负责高冬梅高姐指派的黔版书区的书籍上架整理任务。
第一天,我和女儿花卷完成了三个书架;第二天,又完成了两个书架;第三天,侄儿洪加入进来;今天是第四天,太座的加入让进度更快。从中午一点开始,到下午五点,终于基本完成任务。
惬意的我,感觉完成了几艰巨的一项“世纪工程”,这一个“单元”就有超过十个书架的书籍归类整理和上架工作量啊!然而,这样的书籍分类单元在二十四书香书店,目测有几十个。
秋蚂蚱说过:“读书,使我们从现实中抽离而发现自我。”我在书柜前没有“从现实中抽离”的灵魂出窍,摸着昨晚剃的光头安慰渺小的自己说:天分好,要读书;天分不好,更要读书。书这辈子是看不完的。人生很短,想看的书看看,一辈子过完。
秋蚂蚱还说过:“书店里有什么样的书,就会迎来什么样的人。”以后的每个周末进城,太座去买菜,我和花卷在书店做半天义工,还可以抢先参加店里的活动。我每年在网上买书的预算也可以直接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消化掉了。一群你不喜欢的人,一定开不出一家你喜欢的书店。我那么喜欢这家书店,像我这样的人……实在为这家书店担忧。

关于二十四书香书店
咨询电话:18984593890
微信公众号:二十四书香书店
详细地址:乌当区新天大道北段99号新天卫城“里外里”商业街内
书店2020年12月已迁至贵阳市六广门,并更名为“也闲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