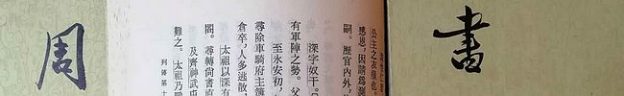新买的书架是九月二十六日到的。用了两个小时安装上,再两个小时把已无架可插四处散放的书和原来架上的书规整规整,书房又秩序井然了。
国庆和中秋在同一天,据说这样的“偶遇”在二十一世纪只会出现四次。这是又一种活久见。
上午洗衣服,收拾家务。午饭后,带女儿去野贤书局(新光店)。她念了好几天要去买书。我们约好每次只买一本,看完了才能再买。上次买的书她第二天就看完,所以今天假期第一天就迫不及待要再去。
去书店路过“开封菜”(KFC),她叹了一口气,说:“特朗普好奢侈啊!”
“啊?他怎么奢侈了?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在网上看到他喜欢吃汉堡。如果愿意,他可以天天吃,你说是不是很奢侈?”
“啊……这……”我竟无言以对。
今天我们各买了一本。她买的是《写在二十四节气里的古诗词:夏》,我买的是郑鸿生《寻找大范男孩》,三联书店二零一三年八月一版一印,定价四十六元,会员八折购入。又去老店二十四书香书店淘了一本旧杂志,二〇〇七年二月一日出版的《华夏地理》,零售价二十元,四元购入。这一期是春节专辑“到西藏过大年”。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去西藏是在六年前,也是国庆长假。
离开书店,顺路去文具店买了一支正红水性笔和十支笔芯。上周买了“英雄”牌的红墨水,结果写不来不红,是深粉色,或者说是紫粉色,总之那种颜色狠奇怪。又重买了一瓶“老板”牌的红墨水,写出来也还是不红,不过比“英雄”更接近红色一点。这年头,不论是“英雄”还是“老板”都靠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