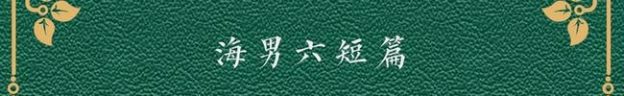“你这个人很不合群,对集体从不关心,自我封闭得很厉害,这可不行啊!你要改一改这些毛病,这毛病可是致命的。人不能脱离社会和集体而独来独往。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参加集体活动就是不道德的。我们奉行的是集体主义原则,绝不允许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她越说越激动,越激动逻辑就越混乱。她还结合自己半辈子珍贵的人生经历,论证了许许多多抽象的大道理。说到动情处,多次掏出手帕擦拭眼泪。我被感动得差一点笑出了声,双手交替着使劲掐户口、掐大腿,终于遏制住了几近喷发的爆笑。——《上火》
我快五十岁了,近来仍有人这样对我说类似的话。太不可思议。如果真正从内心认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就不会对他人提出“合群”的要求,就不会认为不合群是一个问题。读书到头来,还是读自己。
劳马《劳马六短篇》,海豚出版社“短篇经典文库”系列皮面精装“六短篇”第六种,2016年1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76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