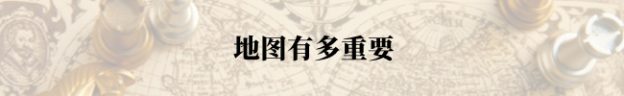阿Kun是这个学期近半才转来的新生,率真、可爱,喜欢拳击。他来到幸福学堂这个全新的学习环境,就像闯进一片陌生森林的鹿,跌跌撞撞,这里瞅瞅那里摸摸,用自己的方式在熟悉和了解这里,而我任教他的中国历史,语文也常常合班一起上,于是也就有了一些关于他与我的趣事。
端午运动会那天,大雨。我把二娃交给幼儿园老师帮忙照看,就忙不迭去给冒雨站在运动场上等待入场的花卷撑伞。伞不够大,我只能搂着花卷的肩膀,尽量保证她不被淋得太湿,因为我不想她周末感冒发烧在家躺两天。阿Kun看到这一幕惊呆了:“豆总!你怎么可以当众搂着女学生?这也太那啥了吧?!花卷你没事吧?!”语气中满是关切。
“这是我女儿啊!”
“女儿?花卷,豆总是你老爸?”
“对啊。”
“哇~花卷你太幸福了,有这么博学的爸爸当你的老师。”阿Kun眼里慢慢都是羡慕。
————
一天午饭后,花卷来办公室:“老爸,有人想认你当干爹,但被我无情拒绝了。”
“干爹?什么情况?人家要认我当干爹,怎么就被你拒绝了呢?”
“我刚才在三近斋,阿Kun问我他可不可以当你的干儿子,我告诉他‘我爸已经有儿子了’,他就失望离开了。”
————
“豆哥,你每次打乒乓球是不是都不认真?”大课间,我被小学二年级的潘神3:0打下后阿Kun问。
“啊?我刚才没有放水啊,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说你认真打球很厉害,学堂根本没有人能打得过你,但是我看你并不总是赢,有时候还败得很惨,就像刚才。”
“哦~传言总有被夸大的成分。比赛嘛,总是会有输也有赢。”
“你不要装了。一会儿你一定要和我认真打。”
“我每一球都是全力以赴的。放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