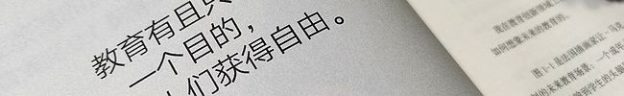种种原因,诸君大多没能按照要求回家与长辈讨论“自由是什么”,于是临时将阅读课调整为讨论课,四个小组5分钟讨论后,选出一位代表来陈述讨论结果。
我以为大家知道怎么讨论,然而发现诸君将讨论等同于聊天。在陈述时,四组都没有代表,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代表——代表自己而不是小组——几乎所有成员都站到黑板前来说了自己的观点。弋涵也站到了黑板前,说出了自己对自由的看法是“快乐”,但小北还是拒绝。不着急,慢慢来。
我通过举例否定了“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观点,将诸君对自由的其它看法总结为几个关键词写在黑板上:自由、快乐、尊重、规则、不伤害、共识,“当大家都在规则之内,互相尊重不伤害,并由此感到快乐,这就是自由的基础。”
我在“共识”这个词下面划了一条线。继续问:什么是共识?
诸君对“共识”这个词的理解达成了高度共识——不同的人有同一个想法。
“不!‘共识’绝对不是统一所有人的思想,让不同的人有同一个想法。”
“那是什么?”诸君问。
“共识,是所有人在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后,经过讨论,大家保持各自的不同达成的共同的目标。”我继续追问:“如果两人或多人的看法一致,是不是就可以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
“也不一定。”虫君说。
“为什么?”我总是喜欢追问“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他们只是想法一样。”墨墨说。
“很棒!独立思考并不代表每个人要刻意与他人不同。只要是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观点,哪怕与他人一致,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先学习一个议事规则,这个规则是教我们如何讨论,怎么开会的,因为要先学会讨论,才能够使独立思考后的观点得到尊重的表达。”
“那是个什么规则?”潘神问。
“《罗伯特议事规则》。”
到此,下课铃响起,发了作业单,提醒诸君,这是第二个六周测评题:
什么是成功
路易斯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一些运气,学会了阅读和书写,拥有了财富和名气。你认为它算不算是一位“成功人士”?与家中长辈讨论什么是“成功”,并将参与讨论者各自的观点以及可能达成的共识在本子上写下来,于下次课交给黎明老师。
歪果仁李思甜:“豆哥老师,这是那种随便的考试对吧?”
“不,这一点都不随便,这是严肃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