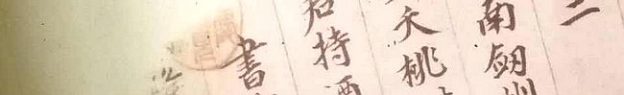早上六点过,早餐前,花卷在房间里关着门读书。听到她读的是七年级语文课本上朱自清的《春》。我不讨厌朱自清,他有学问,只是选作语文课文的这几篇散文,我觉得写得真的不行。就以这篇《春》为例,不干不脆、缠缠绕绕、淅淅沥沥、空洞空泛、华而不实,从时代和其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文本来看,特别是作为教材篇目,实在不是一篇好的范文。难怪作协的一些作家们写起散文来,都是这股子捏鼻子撅腚的扭捏作态;小孩子们一写起散文来都是一股子挺胸收腹翘臀扣手细着嗓子的拿腔拿调小主持人,起势的根子上就做作了。这更让我在编完文言诗词教材之后,要给花卷编一本现代文教材来替代语文课本了。
昨晚花卷睡后,我选了汪曾祺《昆明的雨》和知堂老人的《苦雨》、《雨天的书序一》这三篇文章来,替代七年级语文课本里刘湛秋的《雨的四季》。对我来说,有真情实意,不矫揉造作,好好说话的文章就是好文章。小孩子学写文章,第一要紧的就是要真实,不写假话。
早餐后散步归来,花卷开始在“洋葱学院”上自学六年级数学分数乘法。学完后给我看她的笔记,条理清晰,比我强太多了。“如果字写得再好看一点点就完美了。”我说。
“我知道啊,所以我的课程计划里面也包含了练字。我可以拿一本你的佛经字帖吗?”
“当然。”
我们的大课间,在花园里散步放松时,花卷问:“我早上学了英语,还可以在洋葱学院里学生物和地理吗?”
“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语文安排在什么时间呢?”
“还是晚上。”
“好。你的学习,你可以自己安排,我来配合。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开始触摸到更高阶的学习方式了,那就是自主学习,按照自己发展的需求主动学习,而不是被动的为学习而学习或是被别人安排着学习。我可以问问你学习这些科目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要去体验小升初,体验中考,体验高考,顺便用成绩辗轧我不喜欢的人。”
“体验也是一种学习,但我认为学习更重要的关乎自己,而不是去辗轧他人。人与人的天资与后天环境都是没办法去比较的,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人就出生在罗马;更何况学无止境,一山还比一山高,跑得再快也会有人在你前面,而第一只有一个。那么,你体验了这些考试,然后呢?”
“我要上厦门大学。”
“然后呢?”
“找好工作,这样就可以赚多一些钱。”
“再然后呢?”
“去手账的发源地日本学习,成为手账达人,画自己的胶带,自由自在做自己的手账而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我松一口气,“这可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既然你有这个目标和动力,那爸爸妈妈就一定会支持你。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手账的学者,开创自己的手账品牌和博物馆。”
“嗯,那也不是不可以。那我们现在回家学习去吧,你‘希腊十二神谱系’的自选题我还没有最后完成。”
晚上,刘湛秋的《雨的四季》讲了整整一节课,我觉得好浪费时间,但不讲又不行。我不能直接强势告诉花卷这篇课文不好,我要借课文边栏的提示、引导和提出的问题和她一起分析文章、讨论问题和问题中存在的问题,让她自己作出判断。在这节课开始,满分10分,她给这片文章打了7分。“最后,你把文章里的形容词和语气助词圈出来,圈起来的地方不要读,看看这篇文章还能不能读得通,还能不能读得出要表达什么。”结果,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完整的,更没有内容可言。“所以,这些圈起来的地方就是一个个的洞,这样的空洞太多了,文章就空洞了。”一个小时分析、讨论下来,花卷给这篇文章的分数降到了5分,不到及格的分数。这也就导致我选出来与这篇课文比较的三篇文章没时间讲,只好推到明天继续。还好是自己的娃娃自己的课,快点慢点没什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