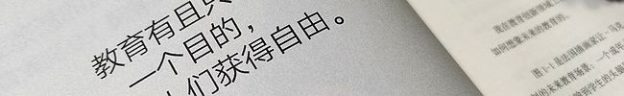9月27日夜,花卷体温39度入院治疗到昨夜出院,12天,她的大叶性肺炎基本痊愈,而我在陪护期间感染了肺炎,今天已是治疗的第五天。
这十几天,我和花卷全靠读书度过。每天她坐在病床上一只手输着液,一只手翻着书,看书累了就做手账,和我闲聊。我这12天在病房里读完了13本书和两个半本。
13本书里,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红色“文艺拾遗”系列的熊式一《八十回忆》、周炼霞《遗珠》、宋春舫《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橙色“文学原创”系列的叶兆言《玫瑰的岁月》、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格非《蒙娜丽莎的微笑》、小白《特工徐向璧》;绿色“学术钩沉”系列的翁同文《中国坐椅习俗》共八本。新星出版社MUJI BOOKS“人与物”系列文库本小津安二郎随笔集《小津安二郎》,商务印书馆“小书虫系列”A.S.W.罗森巴哈《猎书人的假日》和立山“走读历史”系列的《九刺客》;孔学堂书局“贵州杂谈”第一辑中周胜《旮旮角角贵州史》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两个半本,一是线装繁体竖排一函两册苏轼《东坡志林》上册,一是顾远、周贤合著的《教育3.0》。
晚饭前收到也闲书局发来我前日购买的《日知录校注》,繁体竖排煌煌1896页、113万字、上中下三册巨著。
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被后人称为清初三先生。《日知录》为顾炎武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校注者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陈垣校注《日知录》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历时二十余年方才完成。
掌抚摩挲,亦喜亦忧。喜得读好书,忧天资驽钝,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