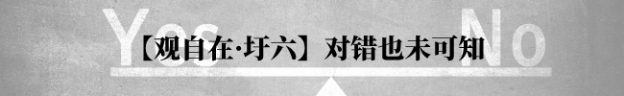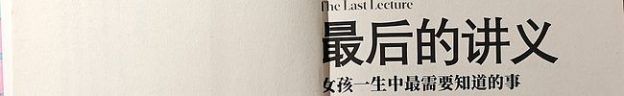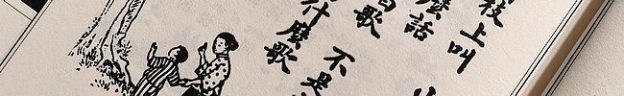每天从家到学堂两地往返共需一小时,在车里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一家人会闲聊一些关于生活、人生的话题。有时是当下的时事,如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有时是两个娃在学校的事,如大娃语文拿了“A”、二娃咬了同学之类。多数话题两个娃不一定能听懂,尤其是二娃太小,但他们能从来自父母的言谈里学到对未来人生的态度。
今天聊了近期的两件事:
一男子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应聘进入某大学任教,但因工作考核不过关被降职降薪后,选择了自杀;一位斯坦福大学博士回国考乡镇公务员。
“对第一件事,我是这样看的”,我说:“出国读书并拿到博士学位,是否回国任教这是一个成年人独立自主的选择。每一个选择的结果,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如果不能接受失败所带来的自然后果,就不应该心存侥幸;如果想全力以赴搏一搏,那就要享受得起成功带来的荣耀,也要承担得住失败带来的打击。所以一个人的内心一定要尽可能坚定、柔和,这样就会变得强大。内心坚定就是清楚,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不论褒贬,都只是别人的看法,与自己无关;柔和就是可以参加游戏、遵守规则并坦然接受一切后果。
“第二件事,斯坦福大学是全球排名前50的大学,能够读到博士,说明具备了相当的学习能力,也应该是某个领域的顶尖人物了。一个全球顶尖大学的顶尖人物,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在自己的领域为后来者放下一粒小小石头,让整个人类的发展能够向前迈出小小一步?但却回国考乡镇公务员,去做一位高中毕业生也能胜任的工作,一位学者接受了什么样的人文教育才会这出这样的选择?”
太座大人说:“虽然每个人的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但从家庭成员的角度来看,第一件事完全有另一种处理方式。例如退出游戏,不要被别人的看法所裹挟;也可以不加入游戏,不被评估。人生要保持弹性。这种弹性是柔和的,不是对抗,这样才能变得强大。第二件事,读了这么多书,却去考乡镇公务员,如果是为了一个‘铁饭碗’,那些书算是白读了。”
我说:“如果是为了饭碗,出国花的那么些钱,至少得有500万吧,如果存下来在银行里吃利息,按照现在极低的利率,一个月也有八千,一年至少有十万的收入,什么工作都不用做也能活得不一定滋润,但肯定自得。所以卷卷,一定要独立,人身的独立、经济的独立、思想的独立。人身的独立,你在18岁时就自然获得了。但这只是独立的基础。”
太座说:“经济一定要独立。经济要独立就要学会管理金钱。不要把钱全部花掉,一定要定期把一部分钱存起来,有了储蓄才会有收益,才有可能实现财务自由。”
“对,所谓理财,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储蓄。”我说:“所谓财务自由,不一定是要有一千万还是五百万的存款,而是账户里时刻都有一笔钱,这笔钱的额度足以支撑你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保持当下状态生活一年时间。经济独立是人身独立的基础,建立在经济独立之上的思想独立才真正算是独立。如果经济独立了,思想不独立,就算是活到80岁也还是一个巨婴。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才是人生第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