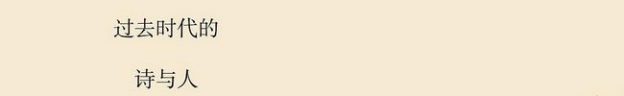李谧在一千五百年前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那如果拥书十万卷会如何?
昨晚枕边书,随手从书架抽了肖恩·白塞尔的《书店日记》,睡前最好读点轻松的。也许。之前看《安妮日记》,努力了两次,每次都读不到第十页,完全无法进入,即便它是独具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献和经典,最后我把它捐给了学堂的图书馆。
十一点上床开始翻书,到口渴起来喝水、屙尿,抬头看墙上的挂钟,竟然已经凌晨一点。不想第二天浑浑噩噩一事无成,赶紧合上书睡觉。
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后,一进书房,还是一股蒜味。开窗通风,又点了一盘藏香,接着看《书店日记》。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喜欢每天早上的这段闲书时间。
蒜味是昨天晚饭后,一家人在温暖的书房一边闲聊一边各做各的事。女儿听故事画画,我翻闲书,把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翻第二遍,太座剥蒜头,今天炒辣子鸡要用。我说:“今天的书房有些五味杂陈啊。”
“人生本就是五味杂陈”太座说。辣子鸡是太座的“辣”手好菜,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辣子鸡,没有之一,尤其是里面的蒜头,香软糯,一锅鸡的精华美味全被吸收在里面。鸡她们吃。
中途在八点半吃早餐,和女儿背古诗,午餐烧烤后洗完碗,又一路不停看到下午三点,就像在游乐场玩溜索,四百一十五页,二十六万字一溜到底。
手上肖恩·白塞尔的这本《书店日记》,应该是去年的年底书店大促销时在二十四书香书店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1版1印。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一家名叫“书店”的书店店主日记,拉拉杂杂的流水账让我欲罢不能,想来可能是因为我的居住环境和书店所在的威格敦有点相似:都是乡下、小镇,镇上人都不多,环境都还算不错;与威格敦相比,我住的这里的不足之处就是那里书比人多,这里唯一一家独立书店在开业一年来,也因经营难以为继而将迁到市内;还有,“书店”书店里有十万书,我只有千余册,还不成系统,也不成主题。
我有一个退休后开书店的梦想(这让我联想到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或者是幻想,但如果真的想要开店,我的阅读量和藏书量实在还是太少。并且,“藏书大家罗森巴哈(A. S. W. Rosenbach)在《谈旧书》(Talking of Old Books)一文中生动地回忆过他的书商叔叔摩西。听闻侄子也想走边藏书边卖书的道路,摩西叔叔认为他完全具备资质:记性好、毅力强、品位佳、文学知识丰富、拥有一定资金。这几条是前网络时代当一名合格书商的基本要求。”如果按照摩西叔叔的这个标准,我看来与开书店无缘了——我记性不够好、毅力不够强、品位不够佳、文学知识不够丰富,还有一条最要命的——资金。
即便如此,也不妨碍我继续淘旧书、读旧书并乐在其中。“在今天整理的几箱书里——也许是牧师藏书的一部分——我发现了两本你准想不到会放在同一个箱子里的书:一本《我的奋斗》和一本来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封面《圣经》。”如果我在箱子里发现这两本书,我的嘴一定会呈“O”型并慢慢张开发出“呜-啊-哇-哦……”的感叹,就和我在觉园禅院走廊壁龛经书结缘处一堆新旧经书里,翻拣到一本全新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大唐罽宾国三藏般若译版,繁体竖排全新《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时一样。
“对大部分从事二手书买卖的人来说,清走逝者的遗物是很熟悉的经历。”我抬头看了看书架上搜买来的新旧大小不一的书,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在与埃科的对话录《别想摆脱书》中说出了我的想法:我可以想象,我太太和女儿将卖掉我的书。不过我活着时仍然会继续买继续读——我又淘到了《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学习掌握那些无法核实的信息。这显然是教师们面临的难题。为了完成作业,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网上搜索必需的信息,但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准确。他们又如何能知道呢?我要给教师们提个建议。他们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要求他们就某个主题找出十条来源不同的信息,并加以比较。这是在练习面对网络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不要为了现成的便利来接受一切。(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