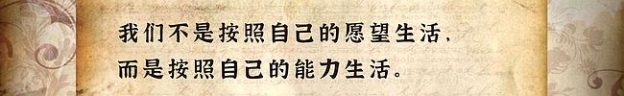上午的导师课时间,是带领自己负责的学生学习《反欺凌政策》。我带领的两名六年级学生,女生早早到教室,男生叫了三次,迟迟不见。出去找,发现他在别的导师教室,问:“你怎么在这里?”学生说已经换导师了。向那位老师确认,说是的。问什么时候换的,说几天前。今天才开学第三天,几天前那就是开学第一天就调整了。去向学部负责人确认,说是家长要求的。原来我作为学生导师,是最晚知道这个消息的。难怪这两天联系家长,对方都态度冷淡,只是简单回复“哦”,“知道了”,“谢谢”。
心情复杂五分钟,就算了。没打算去问家长为什么要求换导师。人和人,就是一场缘。不管是我的还是他人的,机缘未到而已。再说做导师这件事,我也一直不是太接纳,因为除了自己的子女,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当别人孩子的导师。
下午放学前,花卷问我明天带学生去哪里,玩什么,我说了《寻城记2/6》的内容,她决定申请我担任她的导师,加入我设计的活动。我让她先向自己的导师申请。很快得到回复,明天可以加入我的活动,但调整导师需要周五例会讨论。
随后她的导师W老师在微信向我确认这事,我说:“这事她刚和我说了的。我本不想在家是她老爸,上课是她老师,课外还是她导师。但她今天对我说了一番话,让我也无法拒绝——她说班上就三个女生,交不交朋友也没选择;高年级的女生讨论的话题她不感兴趣,玩不到一起。反正在哪个导师组都没有朋友,不如就跟着爸爸边学边玩好了。”
导师觉得花卷还是蛮介意之前与同学发生的一些让双方都不愉快的事,她也有点疏忽,没察觉到花卷的情绪,明天会先和她聊聊,然后换导师的事等周五会议上再讨论一下。
我回复:“这个不是谁的疏忽。学堂班级人数太少,学生的多样性不足,每一个都是个例,这是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现实。只能老师和家长尽力而为,大家努力调整心态。”
有个疑惑,顺便周五例会时问问清楚:由我担任导师的学生更换导师,未经会议讨论就通过,并且作为导师的我还是最晚知道的;我女儿更换导师,由本人提出,家长同意,为什么需要会议讨论?
晚饭时,一家坐在一起,聊到明天去哪里,准备玩什么吃什么,就聊回到换导师和人际关系这事上。我和太座发生了分歧。
太座认为,人应该合群,否则没有办法在社会立足和生存下去。
我认为不合群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尤其是在现在青春期,没有必要为了“合群”而强迫自己去与人交往。真正的朋友是非常难得的,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不做“敌人”也不一定非要做“朋友”,和平共处保持友善互不干扰也很好。并且,如果我们认同人与人天生就是不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那要求“合群”就是一个悖论;如果我们追求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合群”就更是荒诞。一个人,越独立,就越不可能“合群”。但不“合群”并不代表我们就一定是被孤立的孤独者(这个话题,曾经与花卷聊过并记录在《享受孤独:与女儿聊独立思考》),我们只是认可并接纳人与人的“不同”,而不是要靠寻找到“相同点”来得到认同感,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饭后,我在洗碗,花卷在我耳边悄悄说:“爸爸,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
机缘未到,说一千道一万也是徒劳;机缘一到,寥寥数语胜过万语千言。
石头之于六祖,祖知彼机缘不在此,指见青原而大悟。丹霞之于马祖,亦复以机缘不在此,指见石头而大悟。乃至临济之自黄檗而大愚,惠明之自黄梅而曹溪,皆然也。又不独此,佛不能度者,度于目连,亦机缘使之也。(莲池大师《竹窗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