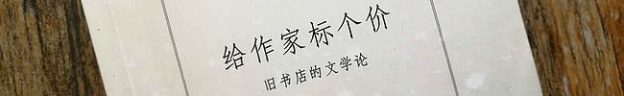新冠康复中,啃不动硬书、大书,只能翻翻不用动脑子的闲书。
李长声《阿Q的长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长声闲话”五种之一,淘来的旧书,2014年8月1版1印,17.4万字,78篇中日之间的文化渊源、文化比较随笔,一日读毕。总阅读量的第1289本。
李长声的书,最早读过的是随笔《枕日闲谈》,中华书局2010年9月1版1印;后来是“长声闲话”系列的《系紧兜裆布》;翻译作品读过藤泽周平的《黄昏清兵卫》、《隐剑孤影抄》。书架上还有李长声的几本书待读,他读书太多,太能写了。另外在2020年6月10日,我读完了藤泽周平“浪客日月抄”四部曲,同时也读完了全部中国大陆出版的12册藤泽周平作品,由此藤泽周平成为我读过作品最多最全的日本作家。没有之一。
虽然是闲书,也有闲收获:
明治以前,日本说诗就是指汉诗,也叫做唐歌,即中国旧体诗。(《蜀山人》)
后花园天皇宝德三年(1451),临济宗和尚笑云担任遣明史书记官出使明朝。使团在宁波逗留三个半月,在北京逗留五个月后,终于在景泰五年(1454)二月踏上归途。行前,笑云游兴隆寺,独芳和尚拿起烧饼问:日本有么?笑云答:有。又拿起枣子问:日本有么?答:有。独芳和尚说:来这里为什么?答:老和尚万福。独芳笑了,赐笑云一卷自注《心经》。(《看明朝那些事》)好一个“老和尚万福”。
我们泱泱大国的书越做越大,不像是给人读的,只宜于壮观书架,可日本经济越不济,“新书”就越好卖,原因无他,唯其价廉也。(《武士家计帐与张大点日记》)这也算是坏事中的好事一件,尤其当下经济更加之不堪,能有便宜新书读,总还不至于让人对生活太过绝望。
董桥散文写得好,但有时觉得像人妖在那里顾盼生姿,美则美矣,不禁起一身鸡皮疙瘩。(《千石的念法》)董桥的散文,我读过几本,有的很好,有的很糟。李长声对董桥的这个评论也妙。
梅原猛认为:“要真正知道日本,必须要知道日本的文化;要知道日本文化,必须要知道《源氏物语》、柿本人麻吕、芭蕉。”周作人说过:“俳句以芭蕉及芜村作为最胜,唯余尤喜一茶之句,写人情物理,多极轻妙。”芭蕉生于1644年,姓松尾,名宗房。十多岁开始作俳句,起初就用本名。而立前后终于开创出自己的风格,即所谓“蕉风”。当时他在深川的住处是一个有势力的鱼商提供的,一间看守鱼笼的小屋子。芭蕉叫它泊船堂,这名字缘于杜甫的浣花草堂,而泊船,不消说,取自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芭蕉在《寒夜辞》中写道:“在深川的三股岸边结草庵,远望富士之雪,近浮万里之船。”有个叫李下的门人送来一株芭蕉,第二年春天茎繁叶茂,院落为之窄,屋檐为其掩,于是人称茅屋为芭蕉庵,芭蕉也就自称芭蕉庵桃青,后来干脆号芭蕉。(《芭蕉的俳号》)我喜爱松尾芭蕉其人其俳句近三十年,今日才得知芭蕉为何为“芭蕉”,可见我的所谓喜爱何其肤浅。去年也大概在此时,我的个人总结PPT用了松尾芭蕉“芒鞋斗笠,春夏秋冬又一年”作结语。今年疫情放开,人人仆倒,个人总结改为提交文字版,少了芭蕉的结语,总觉得肃杀之气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