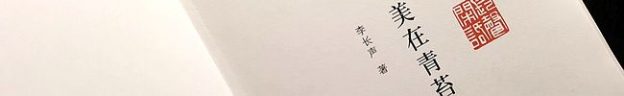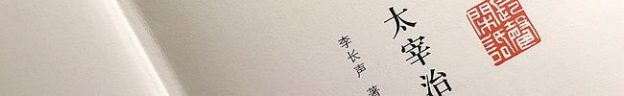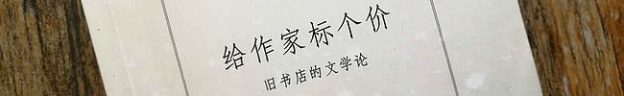2023年读毕的第一本书,李长声《昼行灯闲话》,译林出版社2015年8月1版1印,布面精装,仍是淘来的九成新二手书,12.4万字,42篇随笔。总阅读量的第1293本,读过的李长声的第九本。
这一本,是2012年3月至2014年2月李长声发表的专栏文章合集。“昼行灯”,就是大白天走路提着的灯笼,就是闲扯淡,不过有几篇还算有趣。
1924年,芥川龙之介写了一篇小说《桃太郎》。他笔下的鬼爱好和平,而桃太郎“给了没有罪的鬼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惧”:
“从桃子出生的桃太郎下决心征伐鬼岛。为什么下决心呢?因为他不愿像老爷爷、老奶奶那样去山啦河啦田地啦干活。”
鬼住在远海的孤岛上,“椰树耸立,极乐鸟鸣啭,好一片天然的乐土”。鬼的妻女织布酿酒,跟我们人的妻女一模一样地安然度日,可是,桃太郎打来了。他一手持桃旗,一手起劲儿挥动画了一个红太阳的扇子,号令狗、猴、鸡发现一个杀一个,把鬼统统杀光。狗咬死年轻的鬼,鸡啄杀鬼孩子,猴把鬼姑娘先凌辱在扼杀。桃太郎命鬼酋献上全部财宝,还要交出孩子当人质,饶他不死。
“但是桃太郎未必就幸福度过一辈子。” 当人质的鬼孩子长大成人,咬死了看守的野鸡,逃回鬼岛。鬼经常越海来袭击,烧了桃太郎的房子,猴子也被杀了。桃太郎叹息:鬼竟然这么耿耿于怀,忘了我的不杀之恩。
读芥川的桃太郎总会有一种历史现实感。大正时代有大正浪漫之称,但芥川是现实的,而且预见了今后的现实。(《桃太郎》)其实,当下又何尝不是如此之现实?
我也算爱读书,但不藏书……收藏初版本之类古籍是玩钱,穷人如我者,买的是减价的旧书,图便宜而已……中国有这个歌街,那个街,却没有书店街。旧书店在日本成街成巷,最有名的是神保町,聚集一百多家旧书店,规模为世界之最。(《旧书店血案》)我的近三千册书里,没有珍本、善本,买不起也找不到,因此不“藏”,我买旧书、读旧书的原因,也是因为“穷人如我者”也。外甥前几年不管去哪里旅行,都会淘一本书回来送我。我书架上来得最“远”的书,也都是他送的。这些书里,有一本精美的《運慶ー時空を超えるかたち》竟是初版;还有定价1毛钱的一册薄薄三十几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繁体《徐霞客》,是他在神保町淘来的,花了100円,约合六块五人民币,是定价的六十五倍。这本小册子封面和内页都已发黄变脆,内里还有五幅精美插图。我偶尔从书架上取下来,都是放平在桌上轻轻翻动,生怕力道稍微大一点,整本小册子就会碎成片片蝴蝶。每次看到这本小册子,我都在想,是谁跨越重洋将它带到日本,又怎样流落到旧书店?如果它会说话,这肯定会是一个好故事。
话说日本:书进到书店,价格是出版社定好的,印在书皮上,这个定价受法律保护,书店零售不可以随意提价或降价。旧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店家收来二手书、三手书,自己标上价格,待客而沽。可以说,标价是旧书店的生命线……想买却嫌贵常常是旧书爱好者的痛……有人说,不爱花钱,爱买便宜货,是日本人的国民性,旧书行业也藉以发达。大家把钱包往死里攥,通货紧缩,经济迟迟景气不起来。(《旧书的标价》)而今,街上的店铺十家倒闭八家,还没倒闭的行业普遍都在降薪、裁员,除了生活必需品和上下班(学)一家人开车的油钱,我每年5000元的买书预算,2023年也要砍掉90%,经济不景气到我连三四折的旧书也要买不起了。不过好在家里的书这辈子也读不完,不至于闹书荒,倒是替书店担心。没了书店,出版和阅读环境会更糟糕,好书出不了,因为出版了没人读,越没人读就越不会有出版社出好书,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佐伯泰英写纪实及推理小说,二十年间出版三十本,本本无销路。(《惜栎庄》)这让我想到2023是我敲博客的第18年,敲了200多万字,这得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坚持下来!或许这就是岩野泡鸣所说的“无可救药的兽性勇气”罢!
我向来不相信一本书能改变人生之类的鬼话,除非某人生的大小厚薄还不如一本书。(《任君知日写好书》)所以我从来不去看那种“一生必读的XXX本书”或“一生必看的XXX部电影”之类的内容,且不说其标准如何,人与人的人生又岂能是如此简单就能概括的?不过从每年类似的内容缕缕不绝来看,不肯或不能动脑子,全靠别人投喂的还是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