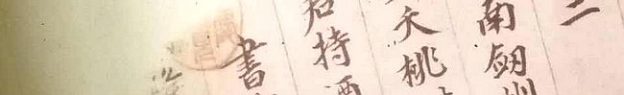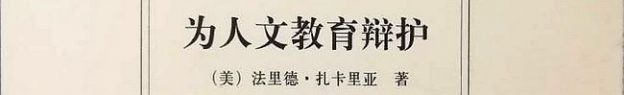昨天四节课,有三节是连堂新课,事发突然没准备,全靠储备。
三节新课里,有两节是高中的中文课。汪博士因身体不适不能继续。从昨天开始,这个学期高中的中文课又是我来接盘了。之所以是“又”,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所以一开始上课,学生就叫我“接盘侠”。
昨天晚饭后花园散步,我对太座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学堂这座山里,各博士、硕士学历的老师们是真老虎,在中学的中文领域我连猴子都不算,只是一粒跳蚤,所以我的全力以赴只为问心无愧。太座除了鼓励我,还提出一个担忧,如果绝大多数人上的是各种公立和私立收费公立教育的学校,女儿一直在幸福学堂上学,未来会不会像她爸爸一样无法融入社会或者为社会所不容?我说:“当绝大多数学校在沿用十九世纪的体制和二十世纪的知识教育二十一世纪的孩子时,我和孩子都去到和绝大多数学校都不一样的幸福学堂,就是想去学习不一样的学习方式。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但可以确定的是,不会是现在这样。”
昨晚九点半在床上看闲书,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困得不行就干脆早早睡了。今早和往常同样时间起床竟还是觉得没睡醒。清早洗完衣服,把这周在布衣书局几乎一元一本拍卖得来的十几二十本书看了看大致分了一下,留下想看和可能会看的,另一半准备周一捐给学堂图书馆。
午饭后进城,太座去买菜,我和女儿去逛书店。自二十四书香书店开业以来,我就保持平均每周去一次书店,每次至少买一本书的良好习惯。感谢开书店的这些好人。书店的存在常常提醒我——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自己不知道的,我的所知极其有限,而无知和愚蠢又实在是深不可测。
今天买了一本米奇·阿尔博姆的《来一点信仰》,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一版一印,硬面精装,定价二十八元。因为护封缺失且封面略有污渍和破损,特价四折十一元两角。看过这位作者的《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不知道这本《来一点信仰》会不会是一本清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