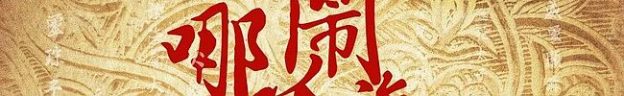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
——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前天下雨,大前天也下雨,更早天还是在下雨。昨天晴了半天,今天从天不亮就又开始下雨。连绵的雨下得久了,我都已经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觉好像一年就雨两次,一次雨半年——贵州的冬天,就是淅淅沥沥从11月到次年4月,好像老天爷也已年过壮年,进入了细细滴滴尿不尽的前列腺中老年。
看来,下雨对我也并非全无益处,至少能不出门就不用出门,省了原本就不多与外界接触的杂事,正好拿来无所事事继续乱翻书,听“秘密后院”的《江湖边》。宅边无柳,有桃、杨梅五六,银杏二三,读书不如“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但说不定哪天我和女儿的二手书店开业,不敢自称“先生”,自号“无用公孙”也无妨。
《雨天的书》是周作人自编集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其中收录的《北京的茶食》一篇,有这么一段: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梁文道在《悦己》中说:“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于是,用这无用的雨天,继《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后,我这无用之人又翻完一本无用的书——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翻书先读序,翻完后我会又重读一遍序,这样虽然只是翻了一遍,但实际是小三遍——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以今天的中国城市为例,虽然建筑是丰富多彩的,但城市外观和布局日趋千篇一律。中国今天地域文化逐渐消失,现代化使中国文化日益趋向同一。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国家情结,认为只要为国家的大一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对地域文化的衰落以及消亡是不会有一丝半点的遗憾的。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民族文化,宏大的国家叙事,无疑在建构强势的国家政权中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能满足那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人们的野心。
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底层的努力,是从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失败,新政权的建立,使国家机器的强化达到顶峰,这是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其实,作为民族的国家和作为政府的国家的强弱经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但作为国家机器是相对很弱的,因为国家的权力被“强民”(或社会)所分化,特别是公民手握有选票这个民主制度最强大的武器,而只有在“民强”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但是在中国,整个20世纪基本上都走的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路子。公民与国家(state)始终是一对复杂的关系,前者始终是弱者,是保护公民利益,还是保护国家利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矛盾,是保护地方文化,还是保护国家文化?无论这些关系对人民和民族有利还是有弊,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在现代化早期,需要加强国家权力以推动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但如果国家权力大到任何力量都无法制约的时候,社会则无法发展,民权则无法伸张。
……
新文化史和微观史使我们从宏大叙事转到日常取向。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风云人物的一举一动,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精英人物身上,视个体的小人物如沧海中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日常、大众、下层,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是人民推动了历史前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红极一时?但很清楚,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领导者为中心的。当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振臂一呼成为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唯恐这样便降低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意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