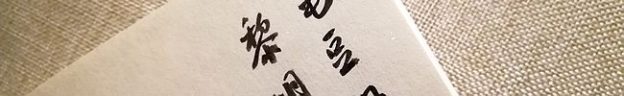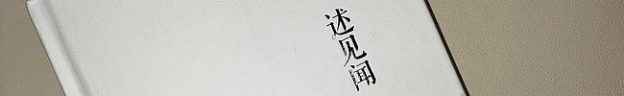在绝对力量前,所有的战术和技巧都是不堪一击。
也闲书局淘书,遇到局座秋蚂蚱,受邀去办公室喝茶聊天,想借口先淘书再喝茶躲开,但这个理由对局座来说不成立。话说,也不知局座哪里来的信心,竟然想诱我在也闲书局做砖开讲座,这事于我就是借十个胆也不敢的,于是顾左右而言他。后续的谈话,在年纪比我大(他六十我四十四),读书比我多得多,人生经历丰富到我在这暗夜里也看不到他尾灯,思考力比我强好几个几何级,思想像无尽的夜一样深邃的绝对力量面前,最好的抵抗就是放弃抵抗,躺平,任强者的思想如洗锅的钢丝球对我从头到脚,从精神到肉身,从死皮到顽垢,一通摩擦,摩擦。一年多去几次也闲书局,是很有必要的,不被局座的思想之箭多洞穿几次,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浅薄和无知。
聊到读过的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书,局座反身从桌上拿起一本旧书,接下来我的操作就是洗耳恭听,然后走个神,想:我有没有读过什么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影响我人生的书?
结账离店,开车回家的一路上我还在想:有没有我读过的哪本书深远影响过我?直到回到家,也没有这么一本书出现。就连字典也不能。只是小时候穷极无聊又无书可读,只好把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翻来覆去看,到最后翻到全书软趴趴松垮垮,封面也不知所踪。现在我记忆里的那本书,还是没有封面的样子。这,算么?这,不算么?应该算。如果没有这本《野火春风斗古城》,就不会有我现在这种报复性的买书和读书冲动。
一进也闲书局,我就像是回到了青春期,总是有一种想要买买买的蠢动。今天在也闲书局购书十四种二十一本,码洋一千二百二十元,实付五百八十四元八角,四八折不到。十四种书录于下,或许里面有某一本能对我产生真正深远的影响——虽然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一点都没有乏味过。
谌旭彬《秦制两千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一年七月一版一印,定价八十八元。这本书是局座推荐的,他说:“毛豆,这本对你上课有帮助。”我说:“好,信你。”
王闿运《湘军志》,朝华出版社“明末清初文献丛刊”之一种,二〇一八年三月一版一印,据清光绪十二年(1886)成都墨香书屋刊本影印,十六卷,定价一百零八元。把书拿到鼻子前,深吸一口气,真香。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下二册),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一九年八月三版,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印,定价一百零八元。局座说如果他推荐人读史,就读春秋战国和民国这两段。我也一直没弄懂,为什么这两段时间天下大乱,但却是人类群星闪耀时,大师如群星一般。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八月一版,二〇二一年七月五印,定价一百一十元。终于,还是买了。
李延寿《南史》第一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六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贵州汽车制造厂宣传科旧书,也闲书局定价十元。《南史》共六册,旧书区有五册,缺第六册,对我来说买一本还是五本都是一样的。买这本,只因读张岱《夜航船》中有句“《南史》:萧贲,竟陵王子良之孙。善书画,常于扇上为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矜慎不传,自娱而已。”自认为,境界不凡,以自娱为最高。
弗格斯·M.博德维奇《首届国会:美国政府的创造,1789—17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十月一版一印,定价六十二元。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二册),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定价七十二元,没有版权页。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全六册),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五月一版,二〇一六年三月七印,定价二百六十八元。
宫崎正胜《身边的世界简史:腰带、咖啡和绵羊》,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四月一版,同年八月二印,定价四十五元。
董桥《小品:卷一》,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四月一版一印,定价五十二元。有天,在哪本书里看到董桥的照片,老来蹙缩,于我想象中的翩翩形象极不吻合,又想起钱钟书说的,喜欢吃鸡蛋不须认识下这个蛋的母鸡。所以,董桥的书,只要没读过,遇到是一定要买的。
黄成《书痴旧梦》,海豚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四月一版一印,定价四十二元。
王强《书蠹牛津消夏记》海豚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九月一版一印,定价一百四十八元。
唐德刚《书缘与人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唐德刚作品集”之一种,二〇一五年二月二版,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印,定价五十九元。
沈迦《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山东画报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十月一版一印,定价四十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