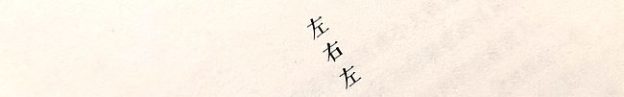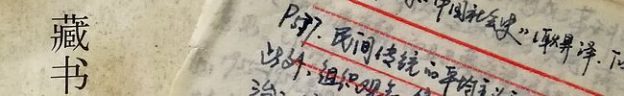闲书是琥珀还是马丽散,就看是讲真话、实话和人话,或者只是用来填充一本硬书与一本硬书之间的缝隙,或是用来填补日常生活中的碎片时间。
钟叔河《左右左》,上海辞书出版社“开卷书坊”第三辑之一种,2014年8月1版1印,布面精装,淘来的八成新二手书,8.2万字,总阅读量的第1296本。前五分之四是各种零零碎碎序与跋,后五分之一接受《财经》和《时代周报》访谈的内容不错。除讲了真话、实话和人话,关于周作人和曾国藩的内容也增广了我的见闻。我都有记下,但不能发出。这书现在看来,早几年出版也是幸事,现在肯定要么删减要么就出版不了,现在“旧的书店里还在卖,发现了就买来读,越读越喜欢。”(《谈周作人及其他》)
我认为他的文章除了美以外,还有真和善。真就是知识,关于人生、自然和文史的知识。善就是能启发你去思想,去追求理性。(《谈周作人及其他》)严格来说,周作人的大部分文章都不是文学散文,而是一种文化随笔,包含了很多社会文化史、科学史、文明史的材料,能够使人对人生、对世界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看法。他很重视这一点。另外,他还很重视写文章要合乎情理,合乎常识。他说,世界上很多反文化的东西、反民主的东西,往往都是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也是不合情理的。周作人文章最可取之处,是将中国读书人的劣根性剖析得最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黑暗面批判得最彻底。(《答客问》)我书架上有三十几本周作人的书,看来是时候好好读读周作人了。
日本侵占中国,周作人没有跟国民党退到西南大后方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多人劝他南下,他却没有南下,这应该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系。鲁迅死后,“左联”一派的人不依不饶地批评他。不仅批评他,也批评所有的“京派”文人,就是非“左联”的人。左翼的文艺青年对周作人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也对这些人是反感的。当然,左派的文人也并不完全等于重庆政府,但对于重庆政府、对于国民党,周作人也从来没有好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周作人在北京应该是属于进步的一方面,他在《晨报副刊》上写的文章,他在北大“出入《新潮》中”,对当时的北洋军阀统治者如张作霖、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章士钊之流,一直都采取批判、不认同的态度。开始周氏兄弟没有闹翻,两兄弟闹翻以后,还是在一条战线上。北洋军阀杀掉李大钊,那时候周作人也完全站在同情李大钊的立场上。左联周扬来管文艺以后,鲁迅对他也是有意见的,而左联对周作人则更加不依不饶。周作人也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要来“领导”文艺,他们自己的“文艺”却根本不行。左联批判梁实秋、沈从文,梁沈他们倒还有文学作品,至今仍然存在,他们也从不说周作人不好,包括冰心和巴金都是承认周作人的。所以,那时候周作人不可能跑到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去,也不可能到延安去。再加上他的家累负担比较重,老婆是日本人,周建人遗弃的那个日本老婆就是周作人老婆的妹妹,也在他家里,要他养着。鲁迅的前妻朱安和母亲住在一起,虽然鲁迅是寄钱回去养家的,但是母亲需要人照料啊,不光是钱就解决问题的。抗战开始时鲁迅已经死了,许广平不到北平去,住在上海租界里,老太太和嫂子还是要周作人管。一家子人,老人、小孩、妇女,只有周作人一个成年男人,不容易逃难。(《答客问》)原来如此。人之为人,不是一拍脑袋一拍屁股一走了之的。
我不藏书,亦少买书,在读书人中也只是个未入流的游勇。(《题赠<毛边书讯>》)如今书本越做越大,越做越厚,越做越华丽,恐怕与书的功能转换有关。过去的书是给人读的,轻便一些总比笨重一些好;如今的书渐变为礼品和摆设,外观和“分量”就成为“首选”了。(《<记得青山那一边>小引》)
书话一词的历史不能算长久,人们写作书话的历史却不能说不长久。手边有两篇宋人“话”《陶渊明集》的,第一篇的作者是苏东坡: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正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另一篇的作者则是陆放翁:
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书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
写的都是读书之乐,而文情并茂,令人于千百年后读之,仍不禁向往,实在是神来之笔,也就是我心目中顶佳妙的书话了。因为古今语不同,古今人情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尤大,今人想用几十个字写出一篇好文章,似已不太可能。(《刘旭源<翻书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