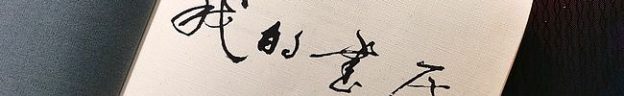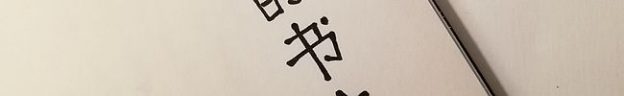感染新冠病毒第五天,康复中。枯坐于炉边一夜翻完董宁文编《我的书房》。总阅读量的第1288本。
这本《我的书房》是2003年4月,《开卷》杂志创刊三周年,以“我的书房”为题向作者征稿的合集。其中不乏周有光、范用、流沙河、何满子、金性尧、许渊冲黄裳这样的名家大家,然也不乏混迹其中的一二蠢货。岳麓书社2005年1版1印。忘了什么时候哪里淘来的。已出版17年的老书,不但纸张发黄,就连六十位作者中也有小半已作古。
回想年青时太幼稚,召祸被戴帽,痛苦得要死,多亏躲在本单位的锅炉房内,读完《庄子》,得以自解倒悬,终身受用。此后又在拉煤拉米余暇,攻读《易经》、《诗经》、《楚辞》、《汉赋》,积有心得,使我不至为新诗所耽误,老来能混一碗饭吃。又后来机关图书馆扫除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数干珍籍被囚禁一室。人事科长怜我贫穷,吩咐说:“你进去住宿,好生看守着,房租就给你免了。”他于我有恩,没齿不敢忘。有书读,那就好。(流沙河《序“我的书房”》)
我的书,没有什么珍本秘籍,明刊宋椠固不必说,就是有限几部略有年头的书,也都是拜长者所赐。自己买的,大抵都是觉得有用、市面也常见的,只是于出版社和作者,常有拣选罢了。比如古籍,如果有多家出版社出了同一种书,我大抵买中华版或上海古籍版;校注本若有多种,则选见闻所及知道够资格的校注者,主编是谁倒是不大在意,因为知道那不过是挂名,以主编者的年龄,对书的质量他多半是不能负责的。这样拣选,只是求其比较靠得住罢了——这也是上过几次当才学乖的。(陈四益《堆书的地方》)
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要改为“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避难所,雅一点说就是“业余做工室”;如果没有书房,我早就自杀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知道我经历的人都会认同。书房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安慰、给了我自信。(龚明德《我的书房》)
摘抄的几段,于我亦然。这些年,我也是全靠阅读自救。现在看来,是一根手指已经摸到了岸。